抗战期间,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重庆。
为启迪更多青年学生走上进步道路,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,一个隐形的“图书馆”在校内悄然建立。
没有人知道这个“图书馆”在哪,却总有一本本红色书籍从中传出,被青年学生广泛借阅。
直到多年后,有知情人著书回忆,人们才得以知道,这个“图书馆”神秘的面纱背后,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“红色书箱”。
隐蔽校外,专人管理
1945年秋天,在中共南方局指示下,革命青年组织——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(简称“新青社”)在国立中央大学正式成立。
此前,国立中央大学内已经建有“据点”(没有名称、不定型的进步青年联络网)。新青社成立后接管了原“据点”的一批进步书刊,并将同学手中的好书集聚起来统一管理,后新华日报门市部又拨过来一部分书籍。
这些进步书籍被统一存放在一个皮箱之中,就这样,一个“红色书箱”诞生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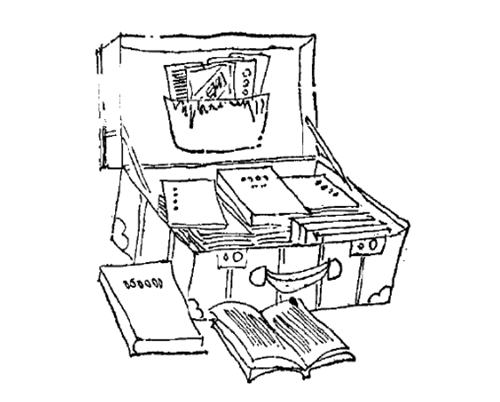
根据 “红色书箱”故事创作的配图(作者:方骏)
“红色书箱”被秘密放在校外,由新青社分派黄可、郭玮等人管理借阅。郭玮谨慎秘密地工作,把书按政治、经济、文艺、历史等分好类目、顺序,编上号码,用复写纸抄写了图书目录单。
为了保证藏书地点、管书人不致暴露,新青社有专人同他单线联系。每次见面交换借书单和图书,都在预先约好的专门地址。除了管理员,大家都不知道书存放在何处。
特殊岁月中,许多走上进步道路的学生,都曾从“红色书箱”里吸收过营养,汲取过力量。
循序渐进,启迪青年
1946年夏天,新青社成员胡甫臣成了书箱的“主人”。为了躲避国民党鹰爪的追缉,胡甫臣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借出图书。
据胡甫臣回忆,自己一般先给人读巴金的《灭亡》《新生》,以及进步的抗日战争方面的文艺作品,建立友谊;然后是介绍高尔基的《母亲》、绥拉菲摩维支的《铁流》、法捷耶夫的《毁灭》、邹韬奋的《萍踪寄语》;再后就可介绍读一些理论书了,如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、胡绳的《辩证唯物主义入门》……
过了一段时间,胡甫臣再把书箱中最秘密的书籍借给同学,如毛泽东的《新民主主义论》等。
当时,很多地下党员和新青社社员都是红色书籍的读者和传播者,原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、曾任南京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许思灏(又名许荏华)便是其中之一。她“着了魔似的”读了许多毛泽东、朱德、张闻天等人的著作,从一个单纯的姑娘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。
为了阅读进步书籍,有同学跑到嘉陵江边,有同学躲进挂了蚊帐的宿舍上铺,甚至有同学把蒋介石《中国之命运》一书的封皮取下,装订在进步书籍上,大大方方地在茶馆里阅读起来。
“白色恐怖似一座囚笼,动辄得咎。我们不能逢人讲共产党、见人宣传共产主义。运用进步书籍从精神思想上启发渗透,是一种恰当的方式。如同几声鸡啼唤来黎明、喇叭唤醒沉睡的青春与勇士……”胡甫臣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回忆。
教授帮忙,巧运书箱
抗战胜利后,1946年5月至10月,国立中央大学从重庆迁回南京。如何把“红色书箱”安全搬运到南京,困扰着胡甫臣等新青社社员。
书箱书籍不可分散,集中一起又容易引人注意。几经研究,一名同学想出妙计:将书捆装好,混在教授的书箱群中,不去管它,由学校统一运输。
大家找到了平素常相往来的心理系教授潘菽,潘菽一口应承。
就这样,这个“违禁”的皮箱被捆上草绳,贴上“潘菽书籍”的标签,混在心理系的书箱堆中,然后被顺利运送到南京文昌桥教授宿舍。
到了南京后,白色恐怖日益严酷。胡甫臣先将“红色书箱”隐蔽在水利系助教王超禹(中共党员)的寝室,后又将书箱转移到鼓楼新村8号许思灏的家中。此后,为了避免危险,“红色书箱”又被转移到一个新青社社员家里,这名社员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,独住一幢花园洋房。
就这样,在那段最紧张的日子里,书箱“住”进了“保险区”。“红色书籍照样进进出出,只是管书取书多跑点腿儿、多辛苦点儿罢了。”胡甫臣回忆道。
参考资料:
《金陵风雨》
《南京大学百年史》